年关将至,冬日的阳光懒洋洋地铺洒着,街上一派繁荣景象,大家喜气洋洋置办年货。“糖果、糖环、年糕、汤圆……”我心里念叨着。其实已第N次大包小包往回搬了,这趟是甜蜜小吃“专题”,故而生怕漏买了哪样,淡化了年味。 忽地,一道明亮的银光晃花了我的双眼,定睛一看,原来是商家出售的米饼印子,俗称“饼印”,是制作米饼的模具,饼印由印箍和印盖两部分组成,印箍圆润如手镯,闪着皎月般光芒,印盖刻着动物、花卉、文字等图案。多久没接触这老物件了?我思绪万千,情不自禁地摩挲着这温暖的金属,印盖凸起的“福”字硌着手心,它像一枚刻着母亲笑脸的甜蜜印记,承载了悠长岁月的浓浓亲情。 
记得儿时生活在农村,小年的炮竹一响,空气里就弥漫着一股浓郁的年味。洒扫除尘,拆洗被褥,备压岁钱,裁新衣,做糍粑,贴春联等,桩桩件件,都是从老祖宗手里传下来的古老风俗,一代一代地延续。打米饼的工艺,是三伯娘从其娘家太平镇带回,并逐步形成家乡的风俗习惯。 一进腊月,主妇们就张罗做米饼,村头巷尾到处飘着诱人的香气。母亲把糯米和粘米按比例分别淘洗干净,晾干后用武火爆炒。这时我和妹妹的“良好表现”总会不失时机,添柴续火的下手活,我俩干得特卖劲,心里却是一五一十地打着小算盘。母亲全看在眼里,手握镬铲却不动声色。米粒可不管人间的闲杂事,它们在镬头里蹦得挺欢呢!“噼噼啪啪”声不绝于耳。炒至米粒稍黄,香气充盈了整个灶房,我和妹妹馋得连咽几下口水,眼巴巴地望着母亲一铲一铲盛入盘,最后一铲了,成败在此一举!“拿碗来——”母亲铲起话音落,眼角的鱼尾纹骤然盛开,像好看的菊花,映着小木窗透进的淡淡阳光,母亲的笑容温暖极了。我和妹妹大喜过望,屁颠屁颠地捧着“美食”享受去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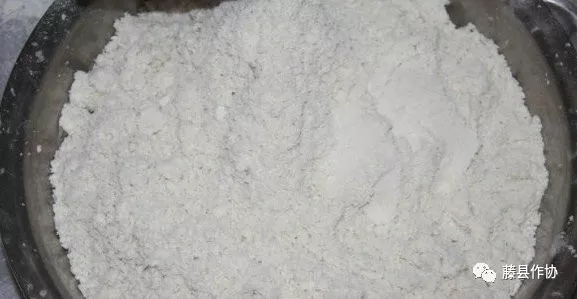
炒好的大米碾成粉末,就到了“润粉”的环节,所谓“润粉”就是把燥热易上火的饼粉回潮。母亲把萝卜薄片埋在饼粉里,让饼粉吸尽萝卜清凉的水分,再换一批萝卜薄片,如此反复两三次,约摸半个月,饼粉的火爆脾性已消磨殆尽,变得温婉可人,任人揉捏,这时就可以做米饼了。 我和妹妹找托盘,抹簸箕,洗饼印,早已万事俱备。母亲炒了花生,拌上沙糖,馅就成了,接着又煎了浓稠的白糖水,和着饼粉在掌心搓擦搓擦,皮就好了,东风也就来了。 打饼模式终于全面启动。我和妹妹做“打手”,负责印饼,而搓粉是一门技术活,不是我等小毛头能胜任的,母亲久经“饼场”,经验丰富,此活就落母亲手中。父亲东瞧瞧西摸摸,哪也插不上手,母亲遂给父亲一肥差:晒饼去。这时年已花甲的奶奶也被惊动,居然“屈就”“伙夫”一职,负责蒸炊米饼。 
犹记得,金属制造的饼印,印盖除了雕刻着惟妙惟肖的花卉和动物图案外,使我最感兴趣的要数那些寄予了美好愿望的文字了,有“丁财两旺”、“福寿双全”、“花开富贵”……还有单独一个字的:如“福”、“寿”、“吉”等,印在饼上,平添几分喜庆的气氛。 我先把母亲搓擦好的饼粉铺在印箍内,用手指旋一个圆坑,接着舀一小勺馅料填入,再铺一层饼粉,盖上印盖,然后用拇指摁压印盖顺时针挪动,直至饼粉和馅料牢固地融为一体,最后连印带饼倒托起来,左手握住印箍边缘,右手向上轻轻一推印盖柄,饼印分离,一枚洁白浑圆的米饼就呱呱问世了。印满一簸箕,奶奶就分几笼蒸炊,新鲜出炉的米饼热气腾腾,香气扑鼻,口感酥软,甜蜜美味。父亲置于阳光下稍作晾晒,以增加米饼的韧性,香味也就更浓郁了。 家家户户打米饼的那段时光,左邻右里互相串门,五嫂八婶三姑六婆齐集一堂,大家互相学习,也互相打趣,一阵阵欢声笑语似乎要把屋顶的瓦片掀飞。笑声掺杂着甜蜜的饼香,是我记忆深处最具人情味的年味。 米饼做好了,母亲用干净的白纸一筒一筒包裹起来,一筒通常为十只。然后叫我和妹妹给附近的孤寡老人送些去。母亲文化不高,却通情达理,心存善念。母亲常教育我们:“对别人关爱就是善待自己,因为有爱,你才不会觉得孤独。”当时对这话一知半解,但日后随阅历加深,终于渐渐懂得。 
年年饼香,岁月悠长,米饼伴随我走过许多甜蜜快乐的时光。后来我离开父母,离开家乡到外地谋生,因为工作和生活的诸多不如意,决定不回家过年。母亲并没有像天下的母亲一样唠叨抱怨,而是托熟人给我带来两筒米饼。我打开包裹纸,浓浓的饼香依旧,我却不是当初那个只为肚儿圆的少年了。翻弄着米饼,并无食欲,忽然,我发现米饼刻划着“快乐”二字,逐一摊开,每只米饼都有!饼印的字在正面,那“快乐”在背面,显然是母亲用利物刻写的。一时间,我百感交集,泪眼模糊。 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儿欲孝而亲不待。”母亲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,我常想,母亲在天堂应该不会感觉孤独,因为她心里满是爱…… “买个饼印吗?”老板的招呼打断了我长长的回忆,对,买一个!回去和儿子一起打米饼印糍粑,让甜蜜的笑靥印满每个日子,印满年年岁岁。
| 